庄子认为,世界万物本来是一个整体,没有界限之分,这就是“未始有封矣”的状态。人生活在“未始有封”的世界,一切都是一体的,自然就没有是非之别。但庄子认为,可悲的是,人类的认识,在主观上分割了这个世界,人类看到了世界万物多姿多彩的表象,继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从此之后,这个“人间世”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有了贫富荣辱之别,有了此是与彼非,自此,而产生了战争、争斗、倾轧。这在庄子看来,是文明的异化,人类画地为牢,为自己营造牢笼而不自知,这正是人类“物于物”的悲哀。

庄子曾痛心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指出,我们在与外物的相爱相杀中,在与世俗搏斗中,都忘记了生命的人生意义,都找不到归路,这是生命极为可悲的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生命的人生意义?庄子认为,我们需要从世界的本体论上去寻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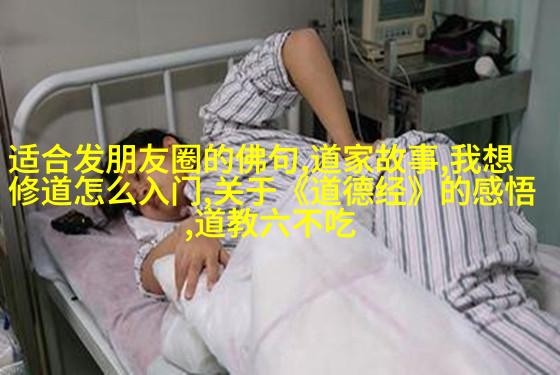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 始 有 无 也 者 , 有 未 始 有 夫 未 始 有 无 也 者 。俄而 有 无 矣 , 而 未 知 有 无 之 果 孰 有 孰 无 也 。 今 我 则 已 HAVE HAVE 称 矣 , 而 未 知 吾 所 称 之 其 果 HAVE 称 乎 ? 其 果 NO 称 乎?
即使如此,我还是要说一说万物形成的问题。宇宙万物形成的问题,如果假设有一开始的话,那就存在一个之前没有开始的情况,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情况前,还应该存在一个更早前的情况,以此推下去,就像开启了一扇窗户,看到了前方的一片广阔天空,但又不知道这片天空里还有多少更多隐藏着的地方一样。在我们眼中秋毫小,而泰山大;彭祖寿长夭短;但如果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的话,你会发现所谓大小寿夭都是相对性的:秋毫固然小,但对比更小的事物来说,它却显得大;彭祖寿长但比起更久远的事例来说,却显得短暂。而泰山虽高,但对比更高的事例来说,又显得渺小。这说明,无论大小、寿夭或其他任何事项,只要你改变视角和参照标准,他们都会变换形态和含义。

所以,从道家的立场出发,要探究生命的人生意义,就必须跳出常识框架,用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和感悟周围的一切。我告诉你们:天下最大的东西,并不是那被人们誉为伟大的泰山,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那些被称作活到老学到老的人,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罢了。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旧不能满足于现状,因为我们的思考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无休止地追求完美和真理。但这份追求,却往往导致我们迷失方向,被自己的想象力所困住,最终陷入一种似懂非懂的情绪状态。在这种情绪状态下,我们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却又无法确证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认知总是在不断变化,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所有已有的知识体系。这是一个永恒循环,让人的思维既充满希望又充满挫折——每一步都仿佛离真理越近,同时又再次证明它其实仍然遥不可及。

因此,对于那些试图解开宇宙奥秘、揭示生命深层结构的大师们,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真的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你们是否意识到,每一次新的理论提出,都不过是在重新确认并加强现有的认知框架吗?你们是否知道,您们正在用您们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的是不是已经超越了一定的范围,而且这些描述本身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一种游戏呢?
面对这样的疑问,大部分哲学家们选择沉默,他们知道,他们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无从回答,更不会触及那个深藏的心灵核心——为什么我会成为我自己,以及我为什么能够成为你。当一个人站在哲学殿堂里,用他的智慧去探索一切时,他却忽略了一件最基本的事情——他自身到底是什么。他穿过时间穿梭回到过去,将眼中的景象记录下来,然后将它们带回未来,再次展现在众目睽睩之下。他把这些事情当成了他唯一可以控制的事情,以至于忘记,他最初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特权,没有特殊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生物中的普通成员之一。当他再次走向哲学殿堂时,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寻找答案,但是每一次寻找似乎总是在原点重复轮回,当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又自动降落回起点。那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这是他的命运,也是我自己的命运,也是所有人的命运。在这段旅程中,最重要的是了解清楚你的位置以及你的责任。你必须学会放手,让一切发生,然后勇敢地接受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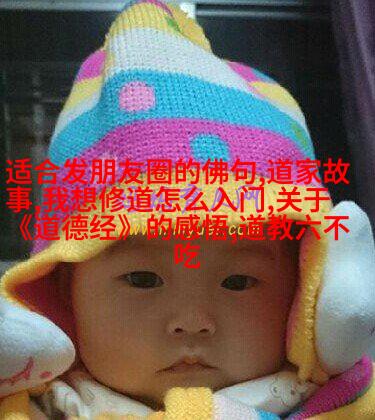
标签: 道教六不吃 、 我想修道怎么入门 、 道家故事 、 关于《道德经》的感悟 、 适合发朋友圈的佛句



